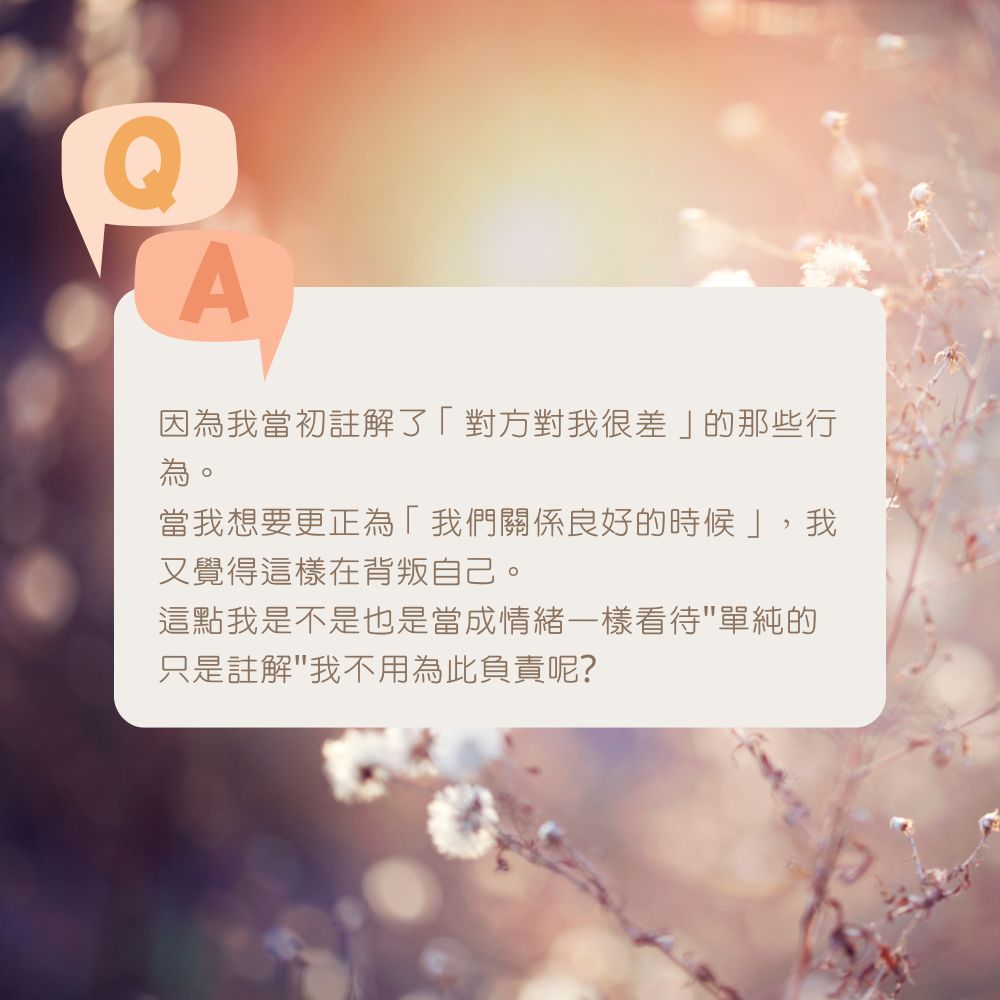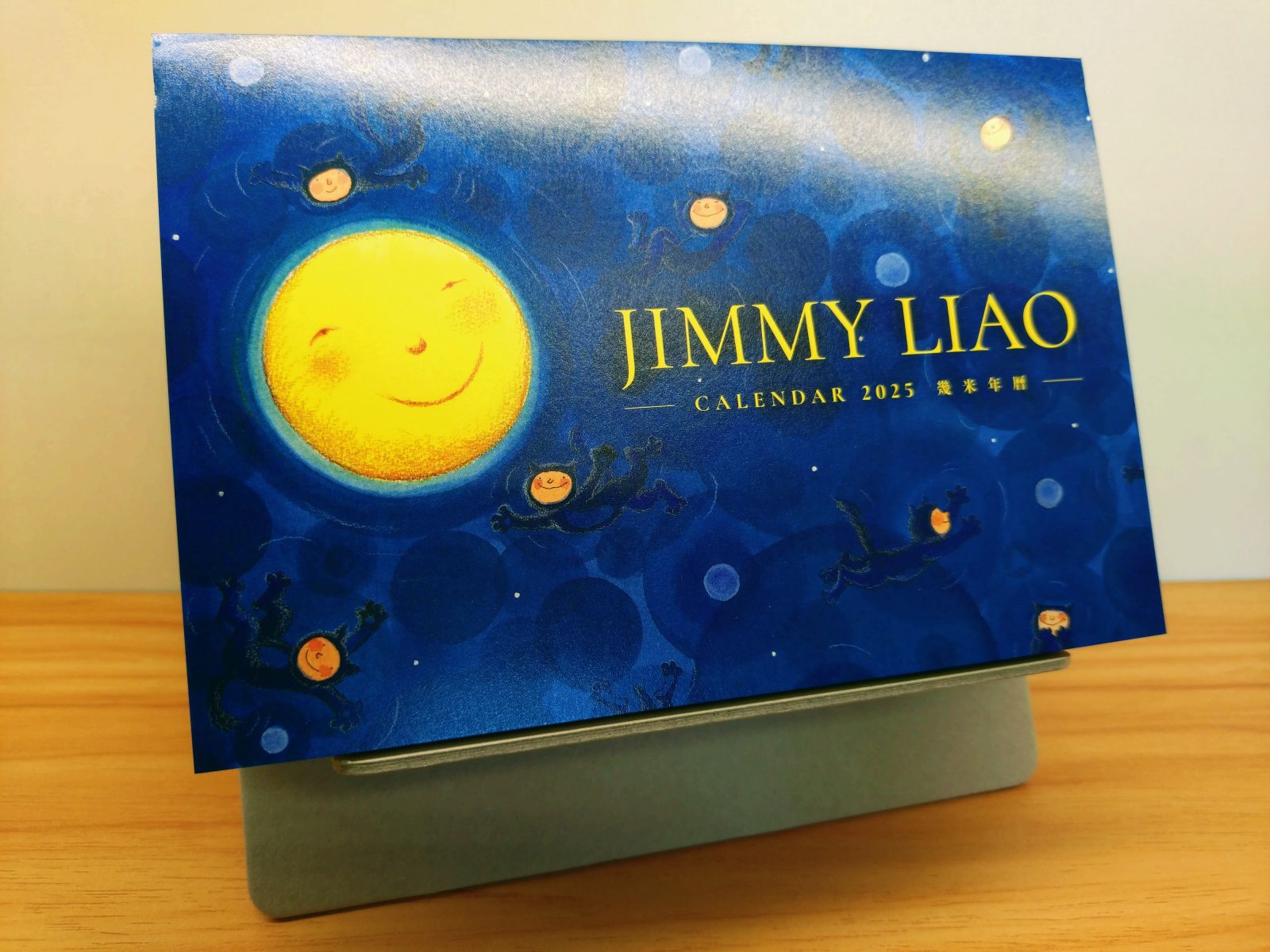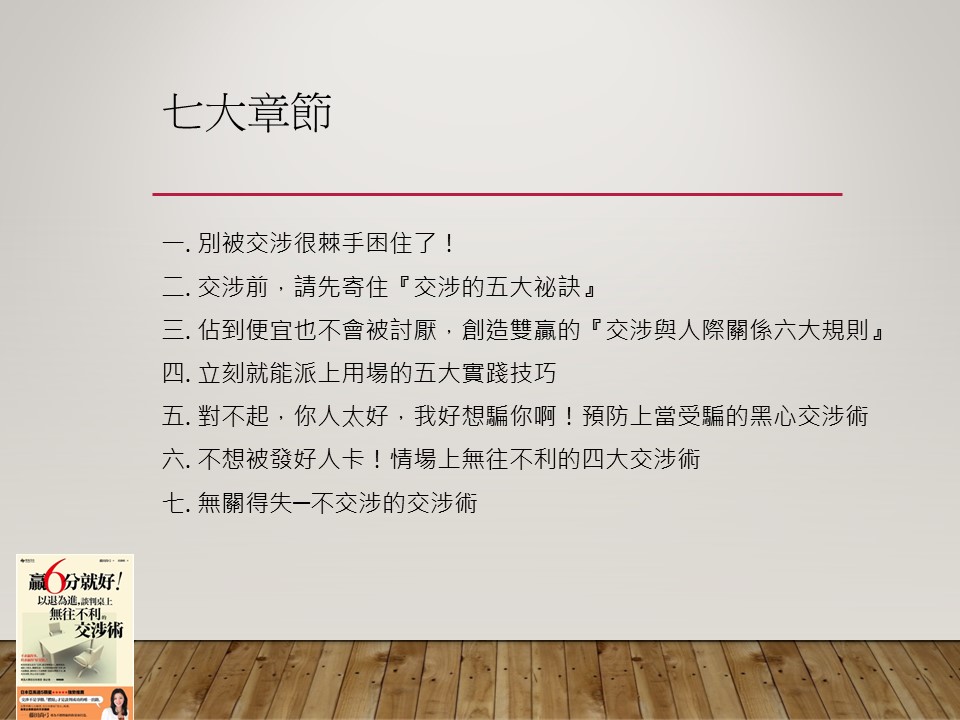這邊提問者的意思其實是因為他當初已經覺得那個伴侶某些行為已經是”對自己很差”,為了練習從否定或負面的句子,這部分是為了轉念,轉化想法,也是為了之後顯化出更美好的關係。
所以他試著從
負面的現況認定:對方對我很差
轉化成→正面的期望的樣貌:我們關係良好
除了頭腦卡住無法自我說服外,同時又產生了覺得這樣是在背叛自己真實的情緒跟感受,好像沒有善待自己,覺得好像背叛了自己。所以來提問。
稍微分享一下
因為這個客人學習了並且看了很多的靈性方法、論述、觀點,包括各種顯化法等,想讓生命變得更好,尤其是情感關係。但也因為可能過多方法的交替使用,反而很難掌握核心跟精隨。常常是變成很努力地去使用正面想法,卻壓抑了真實的情緒,或是逃開看見自己真實的情緒。而我們情緒如果堆積或壓抑得太深,其實常常反而會像是包裹成一層又一層,最終會有更多的”自我覺察”上的偏誤,會誤以為”我已經很正向了”
反到會產生更多的卡點。
後續跟這位客人詢問意願後,也謝謝他願意把自己作為案例,分享自己在靈性上不停努力吸收卻產生很多模糊混淆,充滿困惑的卡點。讓大家藉由這些問答,可以有一些不同的看法跟理解。所以也因此大家看見他的問題的時候,應該也可以看見他發問上的句子、文字的使用,也會有比較多的糾結感。
而關於他這個提問,我對應他的狀況給的回覆是:
註解、念頭、觀念、思想
比如說你看的書內容
如果你沒有產生太多認可或情緒
作用就不會太大
這個問題裡面就有好幾個點要處理
1.你為什麼會一直有覺得需要負責?你要對自己的情緒、念頭負責?
這邊可以先去處理的是
你對所有事情負責相關的觀念下
你去感受這個”我必須對…負責“這個想法的感受去釋放
2.對方對我很差 要轉成 我們關係很好
首先如果你要把客觀事實”對方對我很差”去硬要自我說服成”對方對我很好”
當然大腦會打結
(備註:這邊其實都可以去衍生那些顯化法則中提到的要轉為正向,會出現的問題,比如我就沒錢我要怎麼有富有的感受?)
可以先釐清的是
那些「對你很差的那些行為」
單純的一個一個行為
其實本來也就不等於”關係不好”
就跟有的情侶整天吵架,可是其實也仍然相愛
那可能只是相處互動方式
你可以先去看見「對方對你很差這件事情」
他那些行為 那些可能是你「自己認為」的差
是不是有可能只是你的猜想?
可以先去推翻掉 某些只是你可能自己的主觀認定
再單純的回到對方對你很差
你感受到的委屈不甘心 等
去釋放這邊的委屈不甘心的情緒感受就好了
當你把一些情緒感受釋放掉,你就可以更客觀地去看待這一切
那當然如果很難去轉化這點
你本來也不用去把正面肯定句直接改成「我們關係很好」
妳可以用
“我們的關係越來越和諧美好”
又或者是
“我值得擁有一段甜蜜的愛情關係”
“我們越來越了解對方,並相處愉快”
就不是直接針對客觀的事情硬要去做一個完全不符事件的轉化
這樣你就沒有所謂的「背叛」你自己
3.但關於背叛自己
但比如說你會用到”背叛“這個詞
也要去看見「擔心」背叛自己的情緒感受
還有對背叛這個詞相關的情緒感受去釋放
因為比如我
我很少講到背叛這個詞
我可能只會覺得我沒有能真誠的面對自己的感受
而你特別會用到這樣的字詞跟有這樣的感受
所以代表你對背叛這個詞還是有強烈的觀點或感受
那麼就可以去看見、挖掘跟釋放
※本文提到的釋放法,是萊斯特釋放法(又稱聖多納釋放法、原始釋放法)